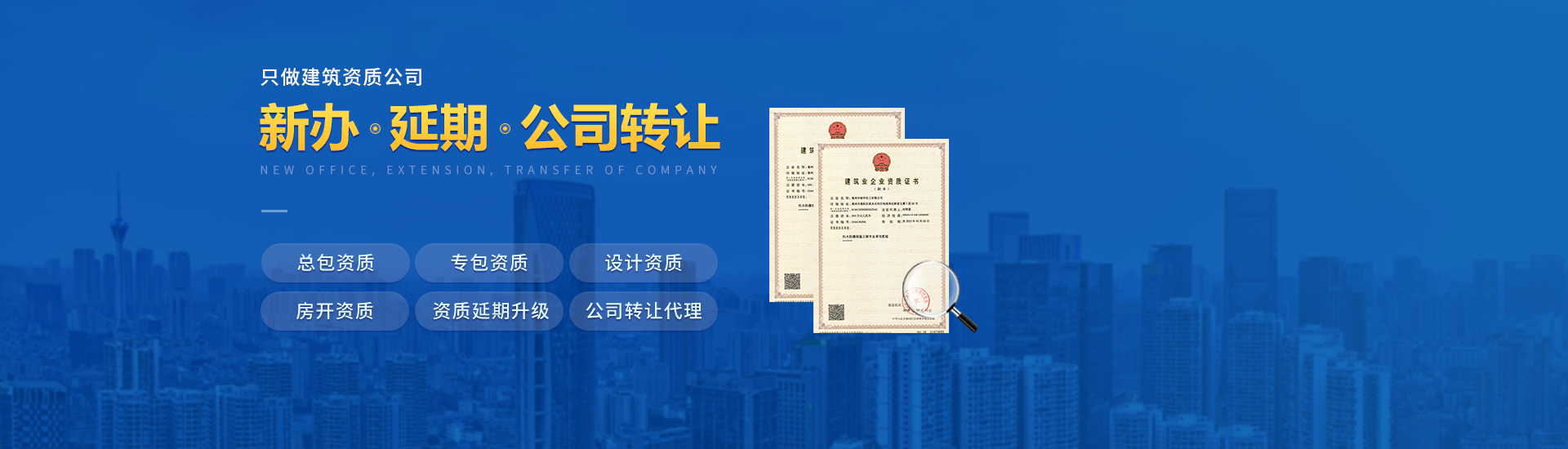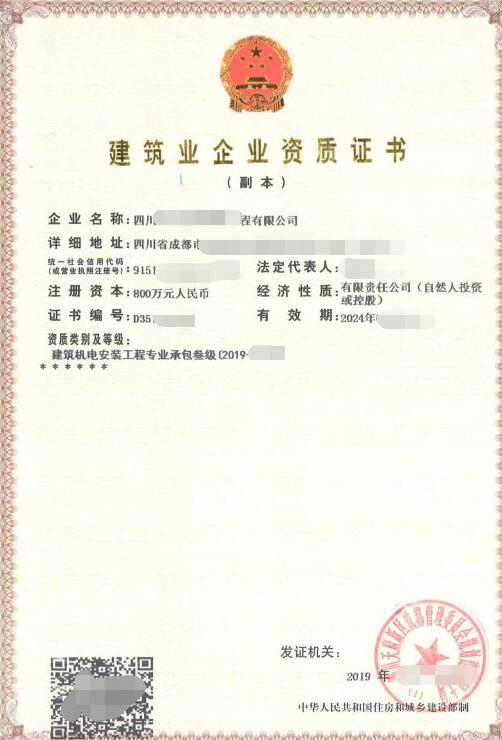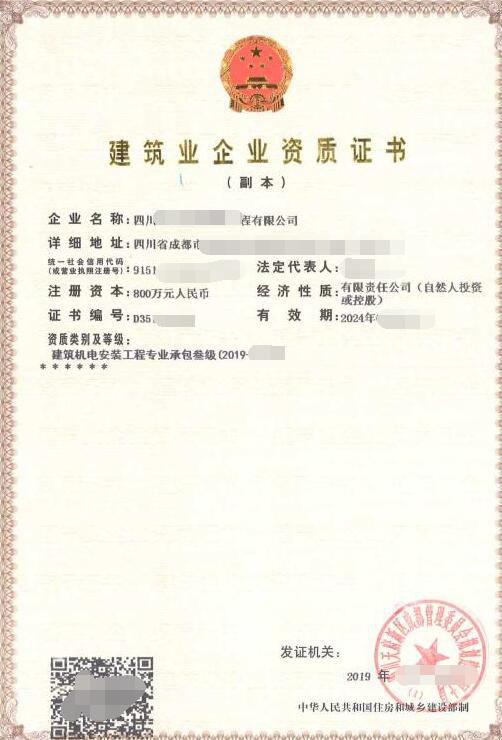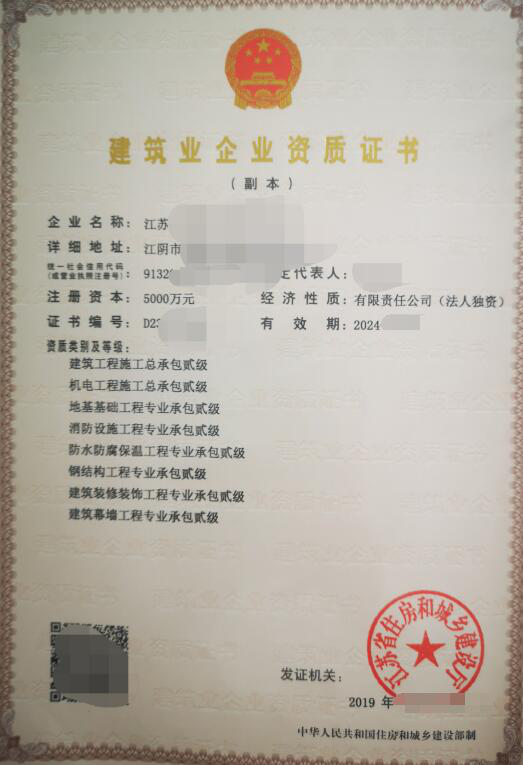在中華文明的浩瀚長(zhǎng)河中,山東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始終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fā)祥地之一,山東不僅是齊魯文化的發(fā)源地,也是儒家思想的搖籃。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山東博物館如同一座巍峨的文化燈塔,守護(hù)著數(shù)千年的歷史記憶,向世人展示著齊魯大地的輝煌與燦爛。
山東博物館(原山東省博物館)成立于1954年,坐落于山東省濟(jì)南市,藏品以富有地方區(qū)域特色的歷史、自然、藝術(shù)類藏品為主,其中陶瓷器、青銅器、甲骨文、簡(jiǎn)牘、漢畫(huà)像石、服飾等收藏尤為豐富,涵蓋了從史前時(shí)期到近現(xiàn)代的各個(gè)歷史階段,堪稱一部立體的“山東通史”。
兩院合并——山東博物館初立
山東博物館的前身可追溯至1904年成立的濟(jì)南廣智院和1909年成立的山東金石保存所。
1887年,英國(guó)傳教士懷恩光在青州創(chuàng)建博古堂,1904年,博古堂遷至濟(jì)南擴(kuò)建并更名為廣智院,這是中國(guó)近代史上最早的博物館之一。
廣智院開(kāi)館當(dāng)天便門庭若市,在這里人們可以看到巨頭鯨、揚(yáng)子鱷、大熊貓、金絲猴等各種動(dòng)物標(biāo)本,冰川、河流、高山等地殼變動(dòng)的截面模型,銀河、太陽(yáng)、月亮、地球的仿真運(yùn)轉(zhuǎn)……大量過(guò)去人們聞所未聞、見(jiàn)所未見(jiàn)的展品,把一個(gè)精彩紛呈的外部世界展示于眾。黃炎培、老舍、胡適等對(duì)廣智院都有很高的評(píng)價(jià),此后“到廣智院看西洋景”成為人們趨之若鶩的選擇。
稍晚于廣智院,1909年1月25日,山東巡撫袁樹(shù)勛上《奏東省創(chuàng)設(shè)圖書(shū)館并附設(shè)金石保存所以開(kāi)民智而保國(guó)粹折》,隨后獲準(zhǔn)。山東金石保存所是國(guó)內(nèi)首家省級(jí)地方政府創(chuàng)辦的博物館性質(zhì)的機(jī)構(gòu)。1929年,著名考古學(xué)家王獻(xiàn)唐任館長(zhǎng)后,著意搜集文物,擴(kuò)充館藏,至抗戰(zhàn)前,藏品達(dá)到17000余件。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zhēng)全面爆發(fā)后,為使珍貴文物免遭涂炭,王獻(xiàn)唐與編藏部主任屈萬(wàn)里、工友李義貴,攜5箱館藏珍品輾轉(zhuǎn)萬(wàn)里,將其運(yùn)至四川樂(lè)山保存。護(hù)寶期間,王獻(xiàn)唐說(shuō):“這是山東文獻(xiàn)的精華,若有不測(cè),我何以面對(duì)齊魯父老,只有同歸于盡了。”李義貴出發(fā)的時(shí)候,剛出生的兒子還不到1歲,而這一守就是13年,直到1950年,這批珍貴文物始返故鄉(xiāng)。
新中國(guó)成立后,地方博物館的籌建逐漸納入議事日程,山東省博物館幸運(yùn)地成為新中國(guó)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座省級(jí)綜合性地志博物館。當(dāng)時(shí)的館址分為東西兩院,東院位于濟(jì)南市廣智院舊址,西院位于濟(jì)南道院舊址。1954年,山東省博物館成立后,將廣智院舊址辟為自然陳列室、濟(jì)南道院舊址辟為歷史陳列室,而山東金石保存所南遷文物中的珍品和廣智院的部分展品則為山東省博物館打下堅(jiān)實(shí)的藏品基礎(chǔ)。
1992年10月,山東省博物館位于千佛山北麓的新館落成開(kāi)放。進(jìn)入新世紀(jì),為了適應(yīng)時(shí)代需求,山東省博物館新館建設(shè)又一次提上日程,新館選址在濟(jì)南市區(qū)主干道經(jīng)十路東段,2010年11月16日正式向社會(huì)開(kāi)放,并更名山東博物館。
山東博物館的建筑外形取自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對(duì)世界的認(rèn)知,上部為半圓形穹頂,下部為四角內(nèi)切立方體。圓,是中國(guó)道家通變、趨時(shí)的學(xué)問(wèn),方,是中國(guó)儒家人格修養(yǎng)的思想境界。圓方互容,儒道互補(bǔ),構(gòu)成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精神,同時(shí)也將齊魯文化剛?cè)岵?jì)的思想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出來(lái)。
山東作為華夏古老文明的發(fā)祥地之一,以“天圓地方”為設(shè)計(jì)靈感,無(wú)疑是最為莊重貼切的隱喻。這份設(shè)計(jì)巧思,賦予了整座建筑一種與生俱來(lái)的莊嚴(yán)雄渾氣質(zhì),哪怕還未踏入館內(nèi),僅僅是遠(yuǎn)遠(yuǎn)觀望,敬畏之心便已在心底悄然滋生。邊長(zhǎng)136米的正方體外觀穩(wěn)重大氣,下部立方體結(jié)構(gòu)在四個(gè)角度進(jìn)行了模式化切削,使四個(gè)角部呈現(xiàn)出棱柱狀結(jié)構(gòu),讓建筑顯得靈動(dòng)而且富于朝氣,避免了方正建筑的古板生硬。正方形上方中央的穹頂采用半圓形白色材料分隔,在兼顧室內(nèi)采光的同時(shí),如同一簇簇向上涌起的浪花,象征著泉城濟(jì)南的“ 天下第一泉”趵突泉,立面采用灰色花崗巖,象征著巍巍泰山。
踏入博物館內(nèi)部,挑高的中庭空間更是震撼人心,室內(nèi)設(shè)計(jì)依然延續(xù)了“天圓地方”的思想,同時(shí),在裝飾方面更具地域特色,黃色的地面象征著母親河黃河,高聳的臺(tái)階象征著五岳之首泰山。在頂部中央,懸浮的墨綠色玉璧如截取了一段春秋夜色——這方300平方米大玉璧的設(shè)計(jì)靈感取自魯國(guó)故城曲阜出土的戰(zhàn)國(guó)玉璧。玉璧中孔與建筑外部穹頂透光部位相對(duì),由此,自然光傾瀉而下,呈現(xiàn)出別樣的光影效果,極具藝術(shù)美感。當(dāng)人們從地下層的史前文明展區(qū)逐步上升至頂層的近現(xiàn)代展廳,如同行走在歷史長(zhǎng)河之中,形成“登臨泰山”般的游覽體驗(yàn)。
無(wú)雙黑陶——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提起山東,今天人們第一印象就是“孔孟之鄉(xiāng),禮儀之邦”,但在孔孟之前的悠遠(yuǎn)漫長(zhǎng)時(shí)間里,山東的遠(yuǎn)古先民東夷留給人們的卻是一個(gè)模糊的背影,先秦時(shí)期,這個(gè)族群曾和西戎、北狄、南蠻并列,曾被視作是落后野蠻的邊緣文明。但當(dāng)歷史塵埃落定之后,人們發(fā)現(xiàn),正是東夷先民摶土成器散發(fā)的質(zhì)樸光澤,閃亮著九州最初文明的晨曦。
“拱著鼻子、張著大嘴、腹部渾圓、翹著尾巴”,眼前這個(gè)萌態(tài)十足的陶器,便是館藏于山東博物館的“網(wǎng)紅小豬”——紅陶獸形壺。它的腦袋和身體像豬,耳朵、四肢和上翹的尾巴又像狗,因此它有了一個(gè)很中性的名字“獸形壺”。
1959年,紅陶獸形壺出土于山東泰安大汶口遺址(距今4500-6200年),雖然歷經(jīng)數(shù)千載春秋,但當(dāng)我們透過(guò)玻璃展柜與它相望時(shí),依然能感受到那原始的生命律動(dòng)——大約5000年前的某個(gè)黃昏,汶河畔一位陶工蹲在陶窯前,望著泥窩里打滾的小豬,小狗翹著尾巴來(lái)回奔跑,晚霞將天際暈染成一片橙紅。他用手中濕潤(rùn)的陶土留住了這天真美好的一瞬,于是壺嘴有了翹起的鼻頭,壺底化作支棱的手腳,色澤明麗,活靈活現(xiàn)。人們說(shuō)器物有靈,或許說(shuō)的就是這樣的瞬間,原始先民把對(duì)生命的觀察揉進(jìn)陶土,從實(shí)用性中涵養(yǎng)出鮮活的靈魂。
今天人們?cè)谙矏?ài)它生動(dòng)可愛(ài)造型的同時(shí),更感嘆它極具實(shí)用的巧妙構(gòu)思,陶壺的所有用途都融入造型之中,使用時(shí)只需從壺尾部注水,在腹下進(jìn)行加熱,再提起背部的把手,就可以將水從小豬嘴里倒出。其形態(tài)下,蘊(yùn)藏著先民對(duì)自然的敬畏、對(duì)生命的禮贊,也是新石器時(shí)代人類精神世界的立體投影。
仰首的紅陶獸形壺并非孤獨(dú)的傳奇,隔著千年時(shí)光,蛋殼黑陶杯的玄色鋒芒正刺破新石器時(shí)代的黃昏。
凝視它,黑暗突然有了重量,在多姿各異的彩陶世界中,它如此與眾不同:空靈精美,體態(tài)修長(zhǎng),通體烏黑。這種神秘的黑色金屬光澤,帶著直觀的視覺(jué)沖擊和震撼,讓人無(wú)限敬畏,眼前的這件陶器名叫——蛋殼黑陶高柄杯。
1929年,在山東章丘龍山鎮(zhèn)的城子崖發(fā)現(xiàn)了距今4000年以上的歷史文化遺址,考古學(xué)家將其命名為龍山文化(距今4000-4500年)。龍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就是“黑陶”,它跟彩陶完全不同,烏黑發(fā)亮,給人一種至純至堅(jiān)之美。其中尤以蛋殼黑陶最為精美,其陶胎之薄,無(wú)與倫比,一般厚度在0.2-0.3毫米,最厚的地方也不足0.5毫米,以“黑如漆,亮如鏡,薄如紙,硬如瓷,掂之飄忽若無(wú),敲擊錚錚有聲”而聞名于世,被世界各國(guó)考古界譽(yù)為“四千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
山東博物館的蛋殼黑陶高柄杯便是其中的翹楚,代表著“黑陶文化”的最高水平,它以0.2毫米的薄胎挑戰(zhàn)著人類手工藝的極限,將新石器時(shí)代的文明推向了難以復(fù)制的藝術(shù)巔峰。今天人們?cè)谔仗ド线€能看到明顯的轉(zhuǎn)輪痕跡,而這正是蛋殼陶薄如蟬翼的秘密——使用了當(dāng)時(shí)世界上最先進(jìn)的“快輪拉坯法”。如此薄壁的陶胎在快速旋轉(zhuǎn)中非常容易破碎,今天人們用電子顯微鏡分析它的成分,用3D打印復(fù)刻,卻始終造不出那份流傳千年的幽光。
蛋殼黑陶并非批量生產(chǎn),耗費(fèi)如此的人力物力去達(dá)到一種極致,也許只有作為禮器才能合理解釋它的存在,用規(guī)范化的系統(tǒng)與工藝極致的器物來(lái)表現(xiàn)祭祀中虛幻的禮儀,這是權(quán)力與等級(jí)的訴求,也預(yù)示著人類社會(huì)新的秩序慢慢形成。作為山東地區(qū)史前文化鼎盛期的巔峰之作,蛋殼黑陶是東夷文化最耀眼、最富有標(biāo)志性的文化符號(hào),而以其為代表的龍山文化也成為中國(guó)歷史上標(biāo)志性的文化發(fā)展階段,它上承大汶口文化,下啟青銅時(shí)代。
商周代序——青銅激蕩的金石之聲
當(dāng)陶器的質(zhì)樸光芒逐漸淡去,歷史開(kāi)始邁入了青銅時(shí)代,青銅器不僅是技術(shù)革命的標(biāo)志,也是先民從共情自然到征伐擴(kuò)張的精神轉(zhuǎn)軌。
展廳中的“亞醜鉞”便見(jiàn)證了這歷史一幕,這尊青綠沁骨的鉞器透雕人面紋,五官微突出,雙目圓睜,嘴角上揚(yáng),口中露出城墻垛口似的牙齒,口部?jī)蓚?cè)對(duì)稱地銘有“亞醜”二字。商代崇尚鬼神和占卜,因此青銅禮器大多塑造出神秘可怖的形象,這是商王借助神權(quán)來(lái)鞏固自己統(tǒng)治的手段,讓人產(chǎn)生一種神圣的威嚴(yán)獰厲之美。
今天人們看到這個(gè)瞪著銅鈴大眼的青銅表情包,或許覺(jué)得呆萌,但它背后卻藏著商王朝最血腥的秘密。1966年,考古學(xué)家在青州蘇埠屯1號(hào)墓發(fā)現(xiàn)它時(shí),還發(fā)現(xiàn)了48具人殉,這甚至超過(guò)了河南安陽(yáng)的殷墟婦好墓。專家推測(cè),這應(yīng)該是商王朝控制下的方國(guó)墓地,因?yàn)殂X在古文獻(xiàn)中記載是“大斧也”,屬于一種斧類兵器,到了商周時(shí)期,鉞代表的是王權(quán)和軍事統(tǒng)帥權(quán),說(shuō)明能夠擁有它的人地位很高,且擁有著強(qiáng)大的兵權(quán),墓主人可能是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類的人物。
既然亞醜鉞如此重要,那為何會(huì)出現(xiàn)在山東境內(nèi)呢?
這要從商王朝和山東淵源說(shuō)起,傳說(shuō)商族起源于山東環(huán)渤海一帶,由東夷族玄鳥(niǎo)氏一支發(fā)展而來(lái)。商始祖契大約與禹同時(shí),因幫助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為司徒,封于商。契的活動(dòng)足跡就在今天的魯西豫東地區(qū)。為對(duì)抗夏王朝、保衛(wèi)自身,商族與東夷族結(jié)成政治軍事聯(lián)盟。公元前16世紀(jì),商朝建立。商王朝采取據(jù)點(diǎn)式的推進(jìn)方式,逐步加強(qiáng)對(duì)周邊地區(qū)的控制。
歷史上著名的盤庚遷殷,說(shuō)的就是商朝第二十代王盤庚,為了避免自然和政治危機(jī),將都城從奄(今山東曲阜)遷都到殷(今河南安陽(yáng)小屯村)。自此,商朝進(jìn)入強(qiáng)盛期,《詩(shī)經(jīng)?商頌》記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而東方地區(qū)因?yàn)閾碛胸S富的海鹽和金屬等資源,更是成為晚商王朝重點(diǎn)拓展和經(jīng)營(yíng)的區(qū)域,隨著商人在東方的統(tǒng)治勢(shì)力持續(xù)東移,相繼控制東部的淄河、游河流域,最終發(fā)展到濰河一線,青州蘇埠屯遺址成為東方邊境線上的重要據(jù)點(diǎn),亞醜鉞在此出現(xiàn)也就不足為奇。
商人對(duì)山東地區(qū)的經(jīng)略,加強(qiáng)了商文化與東夷文化的交流融合,這也為山東地區(qū)融入中原文化圈奠定了基礎(chǔ),但文化融合的背后往往伴隨著征伐。商夷之爭(zhēng)貫穿整個(gè)商代,商代晚期愈演愈烈,這也是加速商王朝覆滅的重要原因之一。據(jù)《左傳·昭公十一年》記載“紂克東夷,而隕其身”,與東夷的作戰(zhàn)耗費(fèi)了大量國(guó)力,而彼時(shí)西邊的周人勢(shì)力卻在不斷發(fā)展壯大,最終間接導(dǎo)致牧野之戰(zhàn)中“前徒倒戈”的潰敗。
隨著周王朝的建立,商人在山東地區(qū)經(jīng)略多年的勢(shì)力逐漸被周人取代,周天子將核心家族分封于齊、魯。齊魯兩國(guó)在不同區(qū)域以不同形式與東夷文化交流融合,歲月流轉(zhuǎn),這片土地迎來(lái)一個(gè)后世廣為流傳的名稱——齊魯大地。